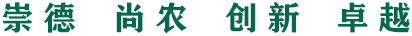在热作人心中,你是我国热作科教事业的奠基人;
在老同事追忆的泪水中,你是雅拉河畔披着荆棘的拓荒者;
当宝岛新村与你的名字叠加,那是热作人永恒的精神家园。你,就是我们心中永远的领路人。
—————题记
2021年7月3日,何康院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
老同志们依旧固执地沿用“院长”称呼,念叨着他在宝岛新村的往事,抚摸着与他在一起时的点滴记忆。
日前,品资所邀请张仲伟、马锦英、邓穗生、何华玄四位老同志座谈,一起回顾老院长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。
张仲伟:“他陪副总理参观时,远远地喊我的名字”
我今年82岁,副研究员,一辈子在院里从事种质资源工作。
1965年夏天,我从北京农业大学(现中国农业大学)毕业,我学的专业是遗传育种。当时,我已经被分配至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遗传所工作,人还没报到,只是档案过去了。
就在这个当口,何康院长把我与另一位同学挖到海南了。
后来听说,何康院长找到国家领导人,通过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彭真同志,再找到学校校长,这才成功地把我们挖了过来。
后来,我们到农垦部报到,工作人员告诉我们,“你们的工作地点在海南,准备去海南岛吧。”
那一年,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共十几个人到“热作两院”报到。何康院长专门与大家座谈。他坐在我们身边,一一询问大家的学习与家庭情况。“哪个学校毕业的”“专业课学了些什么?”大家一五一十回答,何康院长认真地听。
轮到我时,他详细问了我大学四年的学习内容,对我讲起挖我来的经过与目的,“要你们来,就是想开办遗传细胞学科。”
“我们学的也不多。”
“你们总之是学了,好好努力,把学科支撑起来。学科一开办起来,就会把你们调到学院来。”
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坚定地听从党的召唤,党让去哪里就去哪里,从没计较过个人得失。我与同学从未因离开首都到海南最基层的一个村庄里工作而犹豫过、退缩过。
当年,我的大学同学们很多都前往边疆工作,我的老师带了我的四位同学,一起到西藏组建农科院。
报到之后,我安心在院里开始搞育种工作,等待着学科筹建的通知。然而,由于历史原因,学科没有筹建起来,我也就顺理成章地一直从事育种工作。
我第二次与何康院长见面时,已是多年后了。有一次,他陪一位副总理在植物园参观时,远远地看到了我,他冲我招手,“张仲伟,你过来。”
我走上前,他向副总理介绍道:“这是我们的张主管,植物园种质资源由他保存。”我简单介绍了下当时的资源情况,为了不打扰他们就很快离开了。
我只是一名普通的科研人员,与忙碌的何康院长多年不见,没想到他能把我的名字记这么牢。
第三次与他见面,他已调离“热作两院”了。1985年,他返回海南时,黄宗道院长陪着他在院里参观。下午5点多,我在院里碰到了他们。
何康院长依旧记得我的名字,与我交谈时问得最多的还是种质资源。
“院里的种质资源还有多少?”“‘文革’期间损失了有多少?”我一一回答他的问题,他叮嘱我,“千万要保存好,以后会特别重要。”
我回答道:“只要我在这里,就一定会管好。”
何康院长听我这么说,拉住我的手,在马路牙子上坐了下来,缓缓地说道:“当时从北京把你调来,学科也没建起来,我很内疚,很多事情无能为力了。”
我马上劝解他:“都是历史原因,不是你的责任。”
这是我与何康院长的三次交往。我非常敬重他,他平易近人,没有官架子,事业心很强,是我国热带作物学科奠基人。
我从1972年开始搞植物园工作,一直干到1993年。这座植物园能保留下来,也是这位老院长的功劳。
马锦英、邓穗生:“何康院长全家都不搞特殊化”
我叫马锦英,今年79岁了,是高级技工,一直从事木薯杂交、育种工作。
何康院长严于律己,在困难时期,同大家一样过着艰苦的生活,每月定额19斤月供大米,吃“无缝钢管”(空心菜),喝木薯汤。他说:“木薯是宝岛新村的救命粮。”带领大家大面积种植,让大家有东西填肚子。
直到调离“热作两院”,何康院长全家一直住在两居室的平房中,从没住过楼房。后勤部门也曾请他搬到楼房中,他都拒绝了,把数量不多的好房子让给年纪大的科教人员。
那时候信息闭塞,何康院长每次外出归来,都会开大会做报告。“热作两院”人特别喜欢听他做报告,大人孩子都爱听。他给我们讲国内国际形势,数字总是记得特别清楚。他通常要讲两个小时,他讲多久会场里就安静多久,大家全都鸦雀无声地听着。
在他的带领下,“热作两院”人争先恐后地努力工作。拿我们木薯来说,那时候每年都有新品种拿大奖、拿国家奖。我退休后还工作了很多年,我们搞出的大木薯,直径能达到20-30厘米,参加全国比赛,夺得第一名。
我叫邓穗生,今年68岁,是“院二代”,一直在实验室做分析工作。
迁所建院,何康院长把家搬到宝岛新村。困难时期,在我们小孩子眼中,每天看着大人挖野菜,种地瓜,种水稻,海南作物生长周期短,很多东西种下三个月后就有收获。后来,院里还养牛、养猪。生活很艰苦,但总在不停地好起来,那时候的日子过得有奔头。
我与何康院长的小儿子打小就是同班同学,天天一起上学下学。他们的生活,与我们是一样的,一点也不特殊。我的这位同学甚至看到没同学带水、带早餐上学,他也坚决不带,就怕和大家不一样。
后来,我们一起在生产队锻炼,他跟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,跟何康院长一样,处处以身作则。
我从小就生活在“热作两院”大院里,那里丰富的文化生活滋养着我的童年。
宝岛新村离那大还有十多公里,缺乏文化娱乐活动,何康院长对这项工作特别重视。“热作两院”有自己的放映机,能自己放电影,给职工与学生放,也给试验场与周边农村放。
后来,院里成立了乐队,每到周末有舞会与轻音乐会。每逢节假日,院里都要组织文艺晚会,大学生、中小学生、幼儿园的孩子们、机关科研人员都会上场。这样的文化熏陶,在当时海南很多城市,哪怕是海口都无法领略的,那些片段现在回想起来,是如此幸福,至今留在脑海中,无法忘却。
何华玄:“再相逢,我们深情地拥抱”
我是高级农艺师,今年73岁,从事牧草领域相关工作。
我的父亲何敬真,是位森林学家,热作所第一任所长,我是名副其实的“院二代”。1954年,我父亲从老家四川调到广州,因为党中央号召“建立自己的天然橡胶生产基地”,父亲很快带着我们全家搬到海南。
1958年,我上小学二年级,第一次见到何康院长。一天晚上,他来我家与我父亲长谈,我第一次那么近距离地端详他,看着他,心里一直在想,“原来这就是何康院长”。那一晚,他们彻夜长谈。很多年后我才知道,他们在谈筹建热带植物园的事情,要大力发展热带经济作物。
1959年的宝岛新村,生活很艰苦,很多教授自己挑水,自己找柴,粮食不够吃,肉也很少。我与何家的孩子们从小一起长大,亲眼看着他们与我们一样干活。
1979年,我父亲出差为院里挑选椰子种植场地时出车祸受伤,落下终身疾病。后来,父亲为治病经常去北京,为了省钱,住在招待所,就在楼道里熬药。
何康院长当时已回京任职,属于高干。听到这一消息后,他专门到招待所看望我父亲。为了方便治病,1984年,他还想办法为我父亲解决了一套北京住房。父亲的病得到及时治疗,老人活了103岁。我们全家都感念何康老院长的帮助。在那个刚刚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年代,他为帮助我们,想必也顶着很大的压力。
2007年,何康院长回到儋州,前往牧草基地参观,那年我59岁,马上要退休了。我与他的孩子们是发小,他看着我长大,那次相见,我们忍不住深情地拥抱。他依旧记得我们兄弟的名字,记得当年在一个大院里的生活趣事。
我永远记得一个画面,1960年,周恩来总理到“热作两院”视察,我们学生们都赶去合影。我看着何康院长谈笑风生地陪着总理从我身边走过。那一瞬间,他在我们心目中无比伟岸,高山仰止,孩子们对他更加崇拜。
我们家与何家是父一辈子一辈的情义,我们对何康院长是晚辈对长辈的仰望。同样,在“热作两院”人心中,他就是永远的领路人。